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企业群体像中国企业这样高度重视执行。虽然没有认真统计过,但执行显然是中国商业语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细节决定成败”等等,甚至“管理”也是表达相同的意思。也有管理学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战略决定成败”。 并不是说西方企业不重视执行,微妙的区别在于,他们总是说“执行xx”,也就是执行某种目标,或者“谁来执行”,是中低层经理人的职责,但在中国企业那里,执行本身就是目标,高层高度关注。而且有N多管理书籍以执行为名,教人如何执行“执行”,实在很奇怪。不过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
并不是说西方企业不重视执行,微妙的区别在于,他们总是说“执行xx”,也就是执行某种目标,或者“谁来执行”,是中低层经理人的职责,但在中国企业那里,执行本身就是目标,高层高度关注。而且有N多管理书籍以执行为名,教人如何执行“执行”,实在很奇怪。不过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
看看军事,当然也是管理大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怎么说,“如果不习惯于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一条由一系列战斗相互链接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或未设防的地区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就会很容易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唾手可得的成果……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 很多中国企业就是这样不靠谱,由于认为执行本身就有某种价值,是唾手可得的成果,而没有将一系列执行相互链接起来,也不考虑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更没有用战略,也就是最终的结局来衡量各次行动的得失,所以执行总是过犹不及,要么过,要么不及,甚至根本就没有意义。
很多中国企业就是这样不靠谱,由于认为执行本身就有某种价值,是唾手可得的成果,而没有将一系列执行相互链接起来,也不考虑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更没有用战略,也就是最终的结局来衡量各次行动的得失,所以执行总是过犹不及,要么过,要么不及,甚至根本就没有意义。
这种思路有助于理解木桶原理。短板不是比其它板短,而是没有达到最终的结局所需的执行水平。木材永远是有限地,执行执行,经常是达到平均的结果。很多中国企业像真的木桶一样,每根木板一般长,结果尺有所短,甚至只差一步就能成功,寸有所长,又浪费了资源。
更会倾向于执行容易执行的执行。曾有一家企业的行政告诉我,在执行执行的运动中,他被要求起草本部门的执行条例,自己的职责之一是:“当对方发送传真成功,我快步跑向传真机……”而保洁必须将窗台擦到“用力按下指肚看不到灰尘”,我就“武断”地认为他们的管理层肯定不懂业务的执行。
而和业务相关,又容易执行地是销售,可以分割到单件产品,如果经营大头针,更能细化到一分钱。这么说当然不是否认销售工作的重要和艰辛,但品牌、研发和客服等部门,也包括销售体系的建设,必须组成一条完整的锁链,就几乎没有如此唾手可得的成果,远比销售数量的增长缓慢。
中国诸多行业大起大落,去年赚十亿,今年亏十亿。市场兴起初期,执行的压力在销售部门,跑马圈地。但到了产品寿命晚期,故障高发,消费者需求细化,压力就日益转移到后端的部门,完成的销量越大,压力越大,也意味着市场初期投入后端的资源越少,总之,失败的原因就是销售执行地太好了。 中国企业还热衷于多元化。除了政策的风险,在多个市场达到同等且较低的执行水平,显然要比专注于一个市场不断提升执行容易地多,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些市场之间同样也没有相互链接起来,最终的结局是一个大而不强的企业。
中国企业还热衷于多元化。除了政策的风险,在多个市场达到同等且较低的执行水平,显然要比专注于一个市场不断提升执行容易地多,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些市场之间同样也没有相互链接起来,最终的结局是一个大而不强的企业。
更棘手地是相互冲突。据郭士纳(Louis Gerstner)回忆:IBM放弃应用软件市场,因为5000万美元的销售额,激怒该领域的大合作伙伴,停止向客户推荐IBM的硬件,造成10亿损失。当服务部门也向客户推荐竞争对手的软硬件,“一周爆发一次危机”,其它部门“走马灯式地……抗议”,但IBM最终成功地向服务转型。
那些单纯强调战略决定成败的高人,也是因为,如果不考虑执行,战略工作本身很容易执行,仅仅受限于想象力。他们幻想战略仅仅因为自身的宏大,就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和能力,创造出非常规的执行,变不可能为可能。那就也会迷恋行政和销售唾手可得的成果。近50年前,甚至我们整个国家陷入这种狂热。
还是那家重视执行传真和保洁的公司,在拓展活动中教员工玩这样的游戏,以最快的速度依次传递小球,当产生了最快的队伍以后,提出一个远超过其成绩的目标。最后有人想到,将所有队员的手并排相接,让小球从上面滚过去。这个游戏培养想象力和方法论,但“导师”的结论却是:目标决定行动。
光能区分执行的轻重缓急远远不够,更难地是把一系列执行相互链接,因为环境总是处在变化中,那么每个执行,以及链接的方式都要随机应变,保证预期的最终结局只略有调整,就像巡航导弹技术。但很多中国企业的执行并不是“匹配”而是徒劳地对抗变化。
以小见大,不靠谱的执行,反映出中国企业群体处在价值链的低端,高层对基层经理人,投资人和股市对高层的管理,特别是绩效,既短板,又短线。甚至追溯到传统文化,儒家推崇仁和礼,强调执行的动机和形式,忽视结果和内容。“知其不可而为之”更加不只是能力,而是心理的问题了。 克劳塞维茨还写道:“如果指挥官的智力始终集中地用在一系列战斗(就事先所能预见的而言)上,那么他就始终是在通往目标的正道上行进,这样力的运动,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当其分地、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和动力。”
克劳塞维茨还写道:“如果指挥官的智力始终集中地用在一系列战斗(就事先所能预见的而言)上,那么他就始终是在通往目标的正道上行进,这样力的运动,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当其分地、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和动力。”
2006.12.29
本文授权<21世纪经济报道>
 他们明示暗示的社会责任大致分成两类,区别在于和企业运营是否相关。第一类是对社会的“应付款”,企业获得了收益,或造成损失,却没有埋单。又按照相关程度分成三种。第一种主要包括消费者和小股东价值。这是企业的基本教义,如果也算社会责任,那就没别的责任了。不过也牵涉到国情,姑且算作社会问题。
他们明示暗示的社会责任大致分成两类,区别在于和企业运营是否相关。第一类是对社会的“应付款”,企业获得了收益,或造成损失,却没有埋单。又按照相关程度分成三种。第一种主要包括消费者和小股东价值。这是企业的基本教义,如果也算社会责任,那就没别的责任了。不过也牵涉到国情,姑且算作社会问题。 解决之道在于社会从企业外部一视同仁地强制讨债。实际上“社会责任来了”越喊地声大,越说明社会讨债力小。首先,缺乏利益表达和整合的机制,有公信力的中介组织,“应付款”就是糊涂账,其次,各级政府替社会讨债义不容辞,但实际上往往持默许的态度,甚至就是既得利益者,企业欠债的保护伞。最后,相关的社会团体也不够强大。
解决之道在于社会从企业外部一视同仁地强制讨债。实际上“社会责任来了”越喊地声大,越说明社会讨债力小。首先,缺乏利益表达和整合的机制,有公信力的中介组织,“应付款”就是糊涂账,其次,各级政府替社会讨债义不容辞,但实际上往往持默许的态度,甚至就是既得利益者,企业欠债的保护伞。最后,相关的社会团体也不够强大。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虽天纵奇才,他们与世长辞之日,基金会也有信心行使股东权益,支持慈善事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连传给亲儿子,都未必能保证继续正常运营,何况外来的基金会?我们应当先改善公司治理,再谈社会责任也不迟。股东权益还要外部的金融和司法体制来保证。这里也有社会对企业的欠债。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虽天纵奇才,他们与世长辞之日,基金会也有信心行使股东权益,支持慈善事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连传给亲儿子,都未必能保证继续正常运营,何况外来的基金会?我们应当先改善公司治理,再谈社会责任也不迟。股东权益还要外部的金融和司法体制来保证。这里也有社会对企业的欠债。 
 我最终选择了IT业,同时开始打卡的生活。初次见到打卡机的实物,是一个大电子钟样的东西,上面开口,将自己的纸卡塞入其中,一声轻响,再取出来,就记下一个时间。由于从前养成的习惯,刚进公司经常忘记打卡,因此无谓地损失了不少辛苦赚到的工钱。
我最终选择了IT业,同时开始打卡的生活。初次见到打卡机的实物,是一个大电子钟样的东西,上面开口,将自己的纸卡塞入其中,一声轻响,再取出来,就记下一个时间。由于从前养成的习惯,刚进公司经常忘记打卡,因此无谓地损失了不少辛苦赚到的工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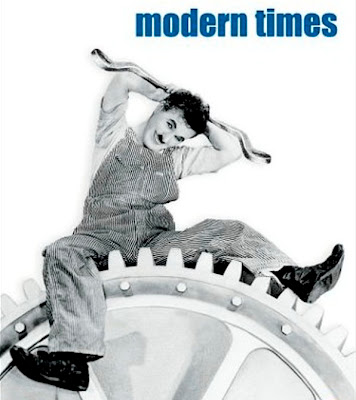 有鉴于此,绩效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像打卡机一样不断进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平衡计分卡,提出并回答顾客如何看我们?(外部角度),我们必须擅长什么?(内部角度),我们能否继续提高并创造价值?(创新和学习角度),我们怎样满足股东?(财务角度)等问题,此外还有一打以上的新工具新方法。
有鉴于此,绩效的理论和实践也正像打卡机一样不断进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平衡计分卡,提出并回答顾客如何看我们?(外部角度),我们必须擅长什么?(内部角度),我们能否继续提高并创造价值?(创新和学习角度),我们怎样满足股东?(财务角度)等问题,此外还有一打以上的新工具新方法。 也许根本的矛盾在于,信息经济发展到今天,在业务上创造力、决策权已经越来越下放到基层,但利益的分配还是高度地集权。管理学者们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网络型组织,但是几乎看不到有人讨论网络型的利益格局。他们都是温良的改革家,或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革自己的命。
也许根本的矛盾在于,信息经济发展到今天,在业务上创造力、决策权已经越来越下放到基层,但利益的分配还是高度地集权。管理学者们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网络型组织,但是几乎看不到有人讨论网络型的利益格局。他们都是温良的改革家,或者也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革自己的命。 狼文化不知何人原创,反正拥护者甚众。其内涵是什么没有共识,在我看来就两个字:狠和忍。更由一本叫<狼图腾>的书发扬光大,甚至立志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但史载明朝中期蒙古犯边,重点抢掠铁锅,抢回去happy地烧水做饭,可见奉行狼文化的组织虽然气势壮观,却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狼文化不知何人原创,反正拥护者甚众。其内涵是什么没有共识,在我看来就两个字:狠和忍。更由一本叫<狼图腾>的书发扬光大,甚至立志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但史载明朝中期蒙古犯边,重点抢掠铁锅,抢回去happy地烧水做饭,可见奉行狼文化的组织虽然气势壮观,却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相比狼群战术,中国企业普遍协同缺乏广度深度,对变化反应迟缓。这种组织和管理的低能,狼文化却指望用个体的激情和奉献来弥补,而所谓奉献,其实是压榨员工。产业和市场形成之初,还勉强能弥补,甚至有更多的短期收益,但随着技术和客户成熟,就纷纷作鸟兽散。明基李焜耀撰文指出:“苍狼式、游牧式的经营模式,对社会总体价值的影响应该是破坏大于创造。”
相比狼群战术,中国企业普遍协同缺乏广度深度,对变化反应迟缓。这种组织和管理的低能,狼文化却指望用个体的激情和奉献来弥补,而所谓奉献,其实是压榨员工。产业和市场形成之初,还勉强能弥补,甚至有更多的短期收益,但随着技术和客户成熟,就纷纷作鸟兽散。明基李焜耀撰文指出:“苍狼式、游牧式的经营模式,对社会总体价值的影响应该是破坏大于创造。” 中国企业则处在两个极端,部分企业家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中国广阔的市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更多的企业善于把握机会,但机会转瞬即逝,就大起大落。具体到这位企业家,直接引发感悟的是两次国际并购的失利,其原因恐怕是外围视野窄,中央分辨率低。
中国企业则处在两个极端,部分企业家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中国广阔的市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更多的企业善于把握机会,但机会转瞬即逝,就大起大落。具体到这位企业家,直接引发感悟的是两次国际并购的失利,其原因恐怕是外围视野窄,中央分辨率低。 如此低水平的竞争就造成众多行业产能严重地过剩。家电、PC、手机等等,起来一个,做滥一个。北极旅鼠的数量会周期性地剧烈增减。传说每当繁殖到一定数目,大群旅鼠就会浩浩荡荡冲向大海或悬崖。同理,低端市场的空间有限,无论怎样狼文化,鹰的重生,还是乌龟爬泥巴,最终都免不了集体自杀。
如此低水平的竞争就造成众多行业产能严重地过剩。家电、PC、手机等等,起来一个,做滥一个。北极旅鼠的数量会周期性地剧烈增减。传说每当繁殖到一定数目,大群旅鼠就会浩浩荡荡冲向大海或悬崖。同理,低端市场的空间有限,无论怎样狼文化,鹰的重生,还是乌龟爬泥巴,最终都免不了集体自杀。 还因为我们总是用传统的思维做现代的商业。儒教推崇仁和礼,似乎只要心诚,装个样子,就能感动天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舆论则同样用道德和文学来审判企业。这边自比苍狼和雄鹰,那边偏说是土狗和山鸡。对企业管理和商业环境没有任何提升,全都是扯淡。
还因为我们总是用传统的思维做现代的商业。儒教推崇仁和礼,似乎只要心诚,装个样子,就能感动天地,解决所有的问题。舆论则同样用道德和文学来审判企业。这边自比苍狼和雄鹰,那边偏说是土狗和山鸡。对企业管理和商业环境没有任何提升,全都是扯淡。
 其次,小企业管理往往是不同地。例如,大公司的每个岗位都高度专业化,小老板和他为数不多的员工却都是多面手,但针对特定问题或情境还是有明确的分工协作,分工的程度虽浅,最难把握地是随机应变。一些从大公司开始职业生涯的创业者,表现反而不如小企业出来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小企业管理往往是不同地。例如,大公司的每个岗位都高度专业化,小老板和他为数不多的员工却都是多面手,但针对特定问题或情境还是有明确的分工协作,分工的程度虽浅,最难把握地是随机应变。一些从大公司开始职业生涯的创业者,表现反而不如小企业出来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差异还体现在企业成长的不同时期。相比大公司重视防范风险,小企业更强调把握机会。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机遇又偏爱有准备的人。但迄今为止,风险管理已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911之后更逆市上扬,而机会管理好像只有风险投资涉足,经理人和商学院还是喜欢从容不迫地讨论宏大的战略。
差异还体现在企业成长的不同时期。相比大公司重视防范风险,小企业更强调把握机会。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机遇又偏爱有准备的人。但迄今为止,风险管理已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911之后更逆市上扬,而机会管理好像只有风险投资涉足,经理人和商学院还是喜欢从容不迫地讨论宏大的战略。 世道快变了。高端管理市场渐趋饱和,要知道,财富500强也只有500家企业。更重要地是,原先的大工业日益差异化,解体成众多细分市场,每个都能容纳一定数量小企业,并且掌握最终客户。大公司则退居二线,为众多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低成本价值,“涵盖他们的能力”。例如PC业和芯片业的代工模式。
世道快变了。高端管理市场渐趋饱和,要知道,财富500强也只有500家企业。更重要地是,原先的大工业日益差异化,解体成众多细分市场,每个都能容纳一定数量小企业,并且掌握最终客户。大公司则退居二线,为众多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低成本价值,“涵盖他们的能力”。例如PC业和芯片业的代工模式。 回头看中国企业,迄今仍然热衷于财富500的排位游戏,对内不惜以行政命令打造产业航母,对外则开展连串激进的并购。也许以中国之大,做大并不难,但做强是另一回事,在管理上有所创新更不简单。此外,500强全部的工作岗位,也只能吸纳中国劳动力的零头。
回头看中国企业,迄今仍然热衷于财富500的排位游戏,对内不惜以行政命令打造产业航母,对外则开展连串激进的并购。也许以中国之大,做大并不难,但做强是另一回事,在管理上有所创新更不简单。此外,500强全部的工作岗位,也只能吸纳中国劳动力的零头。
 普遍的理解,这是由于组织总是用权力奖励业绩,“假设有足够的时间和阶层,每个员工终将晋升到不胜任的阶层,从此停滞不前。”而最根本的原因,人不是上帝,无所不能。庄子云: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怠也。这么说来,彼得原理再也不能更正确,但是再也不能更没用。
普遍的理解,这是由于组织总是用权力奖励业绩,“假设有足够的时间和阶层,每个员工终将晋升到不胜任的阶层,从此停滞不前。”而最根本的原因,人不是上帝,无所不能。庄子云: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怠也。这么说来,彼得原理再也不能更正确,但是再也不能更没用。 传说球王贝利(Pele)最满意自己的进球是下一个,华为的任正非赞扬某个下属进步很大,以前非常差,现在是比较差了。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接班人三选一,当确定伊梅尔特(Jeff Immelt)时,另两人离开,多家财富500强企业虚位以待。他们就做不来GE的CEO,或者其他公司内部绝对没有能当家的人?
传说球王贝利(Pele)最满意自己的进球是下一个,华为的任正非赞扬某个下属进步很大,以前非常差,现在是比较差了。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接班人三选一,当确定伊梅尔特(Jeff Immelt)时,另两人离开,多家财富500强企业虚位以待。他们就做不来GE的CEO,或者其他公司内部绝对没有能当家的人?
 现在我们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彼得原理并尝试加以修正。首先,并不需要假设“有足够的时间和阶层”,其实管理者比他们的下属,包括从前的同事略胜一筹而已,但所处理的任务却繁重地多,通常认为管理幅度是7-8人,可以等同于7-8倍。在这两层意义上,所有的管理者都不胜任。
现在我们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彼得原理并尝试加以修正。首先,并不需要假设“有足够的时间和阶层”,其实管理者比他们的下属,包括从前的同事略胜一筹而已,但所处理的任务却繁重地多,通常认为管理幅度是7-8人,可以等同于7-8倍。在这两层意义上,所有的管理者都不胜任。 那么,为何如此没效率的制度能长盛不衰呢?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组织,从而解决个人再优秀也无能为力的诸多问题。即使一加一小于二,但还是比一大。通过牺牲个人的效率成就了组织的效能。情商至关重要,其中就包含了团队精神。对公司政治、家族企业也不能一概地否定。
那么,为何如此没效率的制度能长盛不衰呢?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组织,从而解决个人再优秀也无能为力的诸多问题。即使一加一小于二,但还是比一大。通过牺牲个人的效率成就了组织的效能。情商至关重要,其中就包含了团队精神。对公司政治、家族企业也不能一概地否定。 队员们庆幸之余,都赞叹队长有神奇的第六感。这件事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经过调查,揭开了真相,实际上并没有第六感。当时的爆炸是由一种罕见的燃烧现象称为复燃引起地:在密闭的空间中,火焰会很快耗尽氧气而减弱,但经过一段时间补充,又会剧烈燃烧。
队员们庆幸之余,都赞叹队长有神奇的第六感。这件事引起了科学家的兴趣,经过调查,揭开了真相,实际上并没有第六感。当时的爆炸是由一种罕见的燃烧现象称为复燃引起地:在密闭的空间中,火焰会很快耗尽氧气而减弱,但经过一段时间补充,又会剧烈燃烧。 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就在<管理者而非MBA>一书中斩钉截铁地说:管理不是科学和专业。前者会导致管理实践出现两种机能失调:“定量计算(过度分析)和英雄主义(假装的艺术)”,后者不同于“工程学的确会运用大量的科学原理”,因此“可以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被人传授”,但是“管理实践很少被人们编辑整理,更不用说验证其有效性了……”
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就在<管理者而非MBA>一书中斩钉截铁地说:管理不是科学和专业。前者会导致管理实践出现两种机能失调:“定量计算(过度分析)和英雄主义(假装的艺术)”,后者不同于“工程学的确会运用大量的科学原理”,因此“可以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被人传授”,但是“管理实践很少被人们编辑整理,更不用说验证其有效性了……” 实际上管理仍然是科学。人类已经能建造登月飞船这样非常复杂的工程,但由于采取标准化的零件,各种参数都人为设定平衡,也许仍然是个小系统。但对突发事件/情境的管理要求在众多不可控因素中迅速找到可控者,相比之下却是大系统。就像气象,永远无法达到物理那样精密,但并不妨碍它构成一门科学。
实际上管理仍然是科学。人类已经能建造登月飞船这样非常复杂的工程,但由于采取标准化的零件,各种参数都人为设定平衡,也许仍然是个小系统。但对突发事件/情境的管理要求在众多不可控因素中迅速找到可控者,相比之下却是大系统。就像气象,永远无法达到物理那样精密,但并不妨碍它构成一门科学。 如此我们能将管理分成三层,最简单地是动作,就像消防队员练习如何使用水枪,破门而入和救助受困市民,这些都运用大量科学原理,并能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传授。然后是情境,这就需要像那位消防队长,需要经历无数的火灾,才能发出自己也不明白,但非常正确及时的警报。
如此我们能将管理分成三层,最简单地是动作,就像消防队员练习如何使用水枪,破门而入和救助受困市民,这些都运用大量科学原理,并能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传授。然后是情境,这就需要像那位消防队长,需要经历无数的火灾,才能发出自己也不明白,但非常正确及时的警报。 不同情境也会相互干扰。几年前我访问一家制药企业时,首先问到研发,这是长期接触IT业的思维定式。东道主委婉地告诉我,国内大部分制药厂都是仿制。因为人命关天,质量控制工作最重要,次之是年审。某期<赢在中国>栏目,评委马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因为只想着控制成本。
不同情境也会相互干扰。几年前我访问一家制药企业时,首先问到研发,这是长期接触IT业的思维定式。东道主委婉地告诉我,国内大部分制药厂都是仿制。因为人命关天,质量控制工作最重要,次之是年审。某期<赢在中国>栏目,评委马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因为只想着控制成本。 中国经济历来机会驱动,显然更接近情境管理,有很多成功案例。规则缺位,想长期打算也不可为。但是近年来,正如德鲁克所说,“直觉管理者”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另一方面,在中层,需要越来越多积累了“第六感”的消防队长,但这不是建几个豪华商学院能解决地,需要无数企业的尸体铺就。
中国经济历来机会驱动,显然更接近情境管理,有很多成功案例。规则缺位,想长期打算也不可为。但是近年来,正如德鲁克所说,“直觉管理者”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另一方面,在中层,需要越来越多积累了“第六感”的消防队长,但这不是建几个豪华商学院能解决地,需要无数企业的尸体铺就。





 时至今日,在英国会计最有望升迁企业高管。法国名牌大学特别是综合工业大学毕业生先进入政府,经过二十多年仕途磨炼,以财务总监的身份进入企业。德国企业高管培养采取双轨制,一条是工程师的专业路线,一条是法学院毕业生担任跨专业的战略工作。
时至今日,在英国会计最有望升迁企业高管。法国名牌大学特别是综合工业大学毕业生先进入政府,经过二十多年仕途磨炼,以财务总监的身份进入企业。德国企业高管培养采取双轨制,一条是工程师的专业路线,一条是法学院毕业生担任跨专业的战略工作。
 为了弥补高管所欠缺的行业经验,通常配备强大的专家团队,包括重金延请外脑。职业经理人深入沟通,把各种专家的行业经验“兑换”成对商业的意义,并加以整合。当然,这种整合有时也多余。福特曾自豪地告诉参观者一辆车有4719个部件。一个工程师后来评价:“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没用的信息。”
为了弥补高管所欠缺的行业经验,通常配备强大的专家团队,包括重金延请外脑。职业经理人深入沟通,把各种专家的行业经验“兑换”成对商业的意义,并加以整合。当然,这种整合有时也多余。福特曾自豪地告诉参观者一辆车有4719个部件。一个工程师后来评价:“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更没用的信息。” 中国商业二十年,也貌似培养了很多经理人。以中国之大,也许会偏重美式的职业经理人,但以国内的差异化,也许会偏重欧式的行业经理人。但实际上更多地是“政治经理人”,在内部是公司政治,在外部是政府公关,都浪费了巨大的资源。无论职业还是行业的维度都难以流动,能力更有待提高。祝他们一路走好。
中国商业二十年,也貌似培养了很多经理人。以中国之大,也许会偏重美式的职业经理人,但以国内的差异化,也许会偏重欧式的行业经理人。但实际上更多地是“政治经理人”,在内部是公司政治,在外部是政府公关,都浪费了巨大的资源。无论职业还是行业的维度都难以流动,能力更有待提高。祝他们一路走好。 引申开来,诸多领域都存在这种不平衡的28划分。刘波把28原则认真地抄在笔记本上,恍然大悟又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图书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人生有了一个重要指南。
引申开来,诸多领域都存在这种不平衡的28划分。刘波把28原则认真地抄在笔记本上,恍然大悟又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图书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人生有了一个重要指南。 四年之后,某外企销售刘波同样将64%的时间精力放在20%的重点客户的20%的重点需求上,于是虽然他口才平平,但还是进入全公司20%的金牌销售行列,一起赚到了80%的奖金,最终得到提升。销售主管刘波同样沿用28原则来管理销售团队,大老板虽然表面总批评他,内心的满意度中等偏上,接近于80%。
四年之后,某外企销售刘波同样将64%的时间精力放在20%的重点客户的20%的重点需求上,于是虽然他口才平平,但还是进入全公司20%的金牌销售行列,一起赚到了80%的奖金,最终得到提升。销售主管刘波同样沿用28原则来管理销售团队,大老板虽然表面总批评他,内心的满意度中等偏上,接近于80%。 刘波关了便利店,在家苦思冥想创业之路。有一天他随手打开一个网页,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国外然后在国内流行的长尾理论。这些理论的拥趸叫嚣着要打倒28原则。正好与刘波的苦恼有关,他感兴趣地看完,又用Google搜索“长尾理论”,惊讶地发现有200多万中文网页。
刘波关了便利店,在家苦思冥想创业之路。有一天他随手打开一个网页,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国外然后在国内流行的长尾理论。这些理论的拥趸叫嚣着要打倒28原则。正好与刘波的苦恼有关,他感兴趣地看完,又用Google搜索“长尾理论”,惊讶地发现有200多万中文网页。 刘波看了很多相关文章,感到一线曙光,但又似乎全无头绪,他非常希望有像28原则那样直观易用的规律。于是又想起了那个古怪的朋友。人造天堂又蹭了刘波一顿饭后,抹抹嘴,说:“我可能发现了长尾理论的精确表达。”
刘波看了很多相关文章,感到一线曙光,但又似乎全无头绪,他非常希望有像28原则那样直观易用的规律。于是又想起了那个古怪的朋友。人造天堂又蹭了刘波一顿饭后,抹抹嘴,说:“我可能发现了长尾理论的精确表达。” 也许更可能是定位某个细分市场,同时提供1%和99%的商品。但最了不起地,可能也是众多长尾理论文章所误读地,是做亚马逊和Google这样既非1也非99或100,而是网络环境或者“存储和流通渠道足够大”的供应商。是这种低成本的平台支持了众多细分市场,转变了28原则,其收益无可限量。
也许更可能是定位某个细分市场,同时提供1%和99%的商品。但最了不起地,可能也是众多长尾理论文章所误读地,是做亚马逊和Google这样既非1也非99或100,而是网络环境或者“存储和流通渠道足够大”的供应商。是这种低成本的平台支持了众多细分市场,转变了28原则,其收益无可限量。